我的家乡在河北阳原。
在我的印象中,家乡既没有历史悠久的名胜古迹,也没有享誉天下的民俗特产,因而也就鲜有人知道。最沾得上名人边的,也许就是大作家丁玲和她那部《太阳照在桑乾河上》了,因为桑乾河就在我家乡那一带。书中描写的“谷子又肥又高,都齐人肩头了。高粱遮断了一切,叶子就和玉茭的叶子一样宽。泥土又湿又黑。从那些庄稼丛里,蒸发出一种气味”的情景,依稀有些印象,但更多的儿时的记忆却是母亲在贫瘠的土地上艰辛的劳作以及那一日三餐赖以充饥的沙沙的能煮开了花的山药蛋和粗粗的橙黄橙黄的玉米面饼子了,和小伙伴们挤在一起晒太阳的时候便幻想着天堂的日子大概就是顿顿能吃上白面做的馒头吧。
但是,最近这几年,我的家乡却突然因为“泥河湾”这个名字而蜚声中外了。因为考古界在家乡的泥河湾发现了大量旧石器和哺乳类动物化石,泥河湾也被国际学术界标定为第四纪地层(即从260万年前到现代)代表地点,其研究价值可与世界公认的人类起源地:东非的奥杜维峡谷相媲美。泥河湾遗址的考古发掘被评为了“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泥河湾遗址群也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仿佛一夜之间,泥河湾,这个河北省阳原县的小山村,成了“神秘、宝地。”的代名词,被冠以 “中国泥河湾”、“中国阳原泥河湾”。!

最早发现泥河湾具有考古价值的还是早在1921年来这里传教的外国神甫。也许是上帝的昭示、天主的惠顾,这位神甫在传教之余闲暇遛弯之间,竟在村周围发现了大量贝壳、蚌类和哺乳动物化石,并以他的知识判断,这里的地质地貌也非同一般。在他把他的发现告诉了同在中国传教的法国古生物学家之后,引起这些外国专家们的极大兴趣,由此也拉开了泥河湾考古发掘的序幕。
令举世震惊的是,随着科学有序的发掘,泥河湾以她独特的古地层和出土的化石、石器竟展现出了一部人类进化的宏大历史画卷! 200万年的马圈沟遗址、136万年的小长梁遗址、100万年的东谷坨、岑家湾遗址、78万年的马梁、雀儿沟遗址、10万年的侯家窑、漫流堡遗址、1万年的虎头梁遗址、5000年的姜家梁墓葬群。,这些熟悉的家乡乡镇村落的名称竟和古人类的进化史一一联系在了一起,怎不令人兴叹!据说,泥河湾遗址发掘出的最具价值的文物之一是一件燧石刮削器,奇妙的是这件刮削器恰巧置于一条大象的肋骨上,且周边散落着许多明显有刮削痕迹的肋骨和可用于刮削的石片等。于是现代人据此展开了丰富的想象,把这一场景描绘成了一幅祖先们在“远古人类的餐厅”饕餮大象的“人类第一餐”。更加令人惊叹的是,这些祖先们用过的随手放在“餐桌”上的“餐具”,竟把泥河湾盆地的旧石器年代向前推进了数十万年,把亚洲的文化起源提前了超过200万年!难怪学者们大胆推断:人类不仅从东非的奥杜维峡谷走来,也从中国阳原的泥河湾走来!

家乡有了如此重大的发现,自然得慕名前去瞻仰一番。于是利用放假回家探望老父亲的机会,选了一个风和日丽的好日子,约了依然在家乡工作的哥哥一道前往泥河湾遗址。虽然我们开的是一个底盘较高的皮卡车,但依然一路崎岖颠簸,显示出拜谒古人类遗址的不易。在经过了一座由威武的大象和凶猛的犀牛以及它们的牙齿构建的大门一样的标志性建筑后,我们终于进入了“古人类的村落”。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巨大的古人类头像的雕塑,外貌酷似周口店发现的北京猿人头颅,但在这里被雕塑家加上了一头浓厚飘逸的长发,显得更加悠然俊秀,在阳光的照耀下傲然注视着前来瞻仰的后人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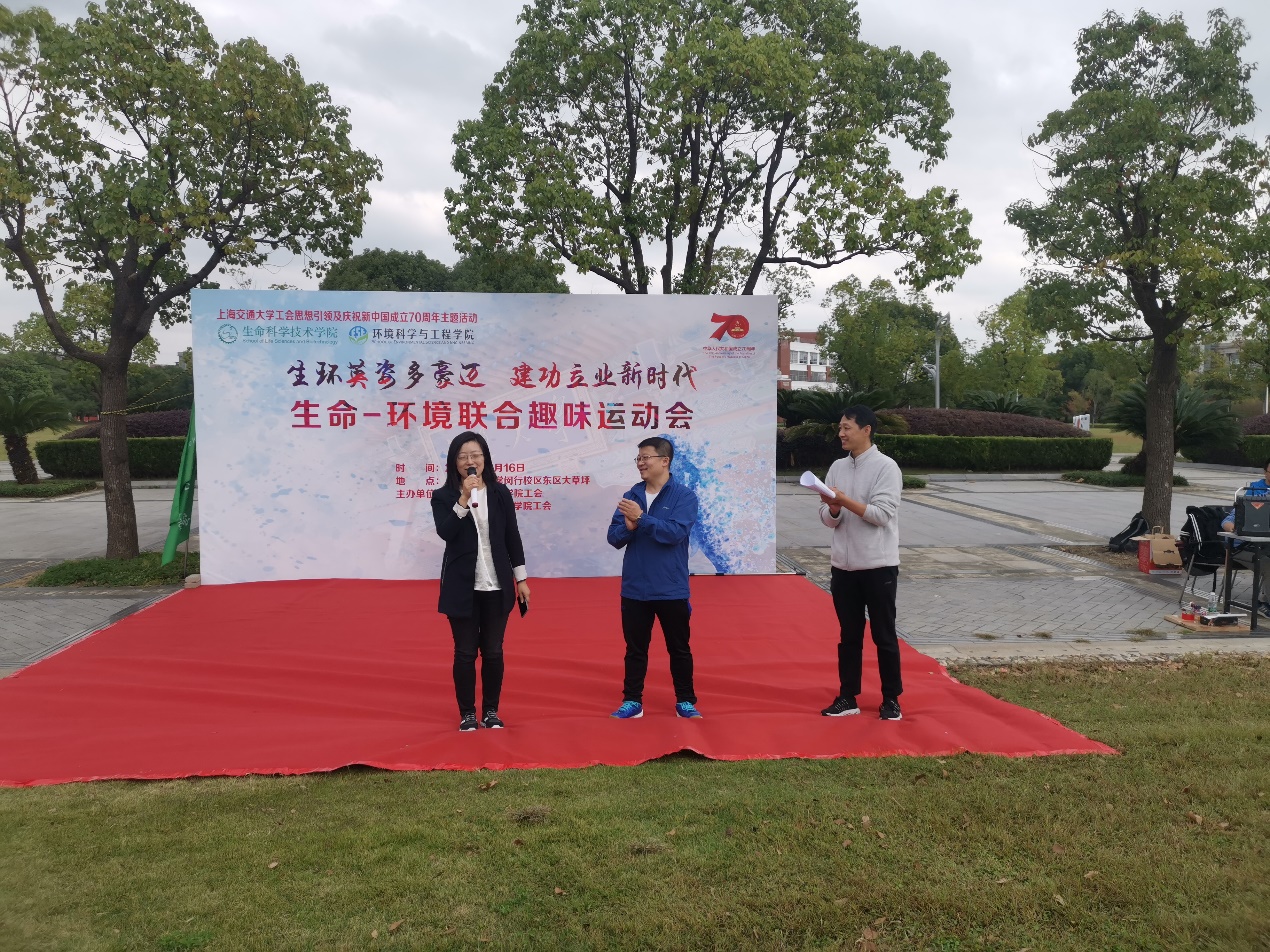
站在山坡的高处,俯瞰泥河湾遗址,满眼的是那层层叠叠、纵横交错的山丘和沟壑,间或分布一些大小不一、错落有致的台地。那些显然是人工挖掘的整齐有序的巷道串联在山丘之间。眺眼望去,远处似乎还平铺着一个很大的平原一般的谷底。这里没有竖起我想象中的大规模的保护性建筑,也没有电视里常看到的那些带个小锤、小铲在现场挖掘的考古工作者。我努力地在想象我们的祖先们在这里生活的场景,恍惚间仿佛那层峦叠嶂的山丘变成了古人类的城堡,而那平坦有致的巷道便是城堡间的“交通要道”了。看来真是隔行如隔山,我这个说起来也是从事环境研究的人,也实在看不出其中的奥妙,肉眼凡胎,只能闭目遐想了。

还是现场展示的文献资料帮忙解了惑,原来早在200多万年前,这一带气候温暖,雨量充沛,有茂密的丛林,广阔的草原,还有一个水域面积达到9000多平方公里的偌大的湖泊。大湖四面环山,烟波浩渺,湖水清澈,鱼蚌不惊,成为了古生物的乐园!在这百花争艳,充满生机的原生态地域,我们的古人类也就伴随着从最早的生命体单细胞生物到海藻类微生物、从无脊椎动物到脊椎动物、从水陆两栖的哺乳动物到恐龙等爬行动物、最后到灵长类动物猿类的生命和人类的进化史一路走来!相对于地球已长达45亿年的高龄,200万年不过是弹指一挥。然而就是这弹指一挥间,实现了从爬行到直立、从模仿到思维、从原始狩猎到制造工具的质变和飞跃!这东方古人类由猿到人的伟大飞跃就是在我眼前这块看似贫瘠的土地上蝉变升华的吗?站在这片在苍凉的地表下由层层土质和片片化石记录了人类进化史的遗址古迹面前,我不禁涌起一种登高台而“念天地之悠悠。”的感慨!
星转斗移、沧海桑田。大约在1.8万年前,由于第四纪冰川期剧烈的气候变化和地壳运动,导致这一带湖底上升,土体交错,那孕育了东方古人类的大湖也逐渐流失干涸,露出了宽广开阔的平原,逐渐形成了今天绵延起伏的丘陵和沟壑,也将那猛犸大象的遗骸以及祖先用过的石片、石球深埋地下,只留下桑乾河依然用她那并不丰裕的水流吟唱着沉淀了百万年记忆的古老歌谣。天哪,原来如此!何时日月轮回、乾坤翻转,再把那浩瀚大湖还我家乡!重现天人合一、万物兴荣的生态乐园!
记得第一次带我妻儿回阳原老家省亲,好奇的女儿问我:“阳原”这个名字是从哪儿来的?我随口答道:也许是祖先们以为这里原是太阳升起的地方,故起名为“阳原”吧。这明显带有虚荣和忐忑的杜撰,年幼的女儿居然信了,未再追问有何出处或依据。今天,那被发掘出的深埋在地下的泥河湾的故事,科学雄辩地向世人昭示:这里就是东方人类的祖先最早看到太阳升起的地方!一种发自心底的对家乡的自豪和骄傲在那浓浓的故土情怀中冉冉升腾,这自豪难以言表,这骄傲无法谦虚!
啊,我家乡的泥河湾。
何义亮
2013年2月于上海
笔者白描:
何义亮,上海交通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工学博士,博士生导师,水污染控制设计研究所所长。2006年美国佐治亚理工大学访问教授,2003年日本国立歧阜大学访问学者。
